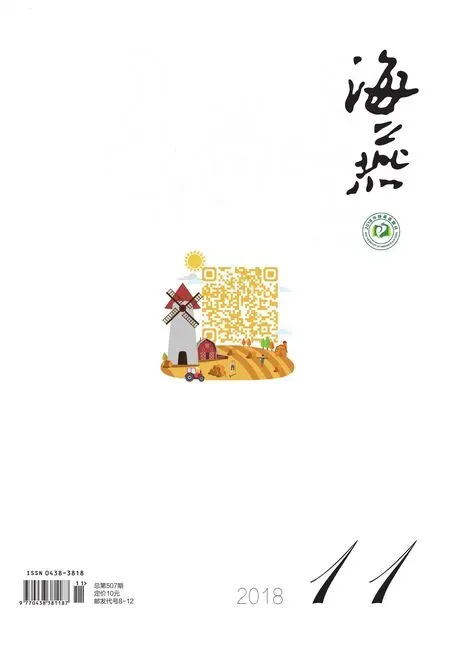我的父親母親
□羅振亞
父親晚年最怕提“老家”兩字
自從撞上老年癡呆這個赤發(fā)鬼
活蹦亂跳的陽光和人事
便在父親的腦海中沉沉睡去
他除了認得老伴兒兒女
汽車也不過是路邊行走的樹樁
只要吃飽喝足
就是老子天下第一
可他最怕提“老家”兩字
只要一提老家或李向陽屯
過去多年的人事細節(jié)就會復活
從他的嘴唇上紛紛站起
想按都按不下去
什么院子里犬吠雞鳴
還有莊稼地豆綠麥黃
屯中間老張家的瘸姑娘對不住馬大平
西頭有錢的王小國娶了東頭的李三妮
欺負人的程水保鐮刀饒不了他
挨餓那年你爺爺差點一命歸西
西南地適合種谷子甜菜
黑土地上沒有河照樣肥沃
說到興頭上他激動不止
一會開口大笑
一會淚流滿面
鄉(xiāng)愁早如村頭那棵老榆樹
根深葉茂鋪天蓋地
每逢這時
我和弟弟都相視一笑
再想聊的話題也先放下
扯扯東歐戰(zhàn)爭韓國總統(tǒng)下臺
再說說天氣預報明天有雨
這樣他就會安靜得像貪睡的孫女
習慣地看看墻上掛鐘的走針
開始用右手數(shù)左手手指
一株麥子的幸福
車輪不都是向前用力的
有時它離目的地越來越遠
父親選擇性遺忘的阿茲海默
反復回放著每一個日子
在蔥綠的往事田地里
麥子一株一株地復活
陽光一吹都想說話
父親常記不起自己名字
但能測出麥地的畝產收成
麥芒的紋理與土質的關系
西南地今年的莊稼長勢
還不斷對著別人喊
兒子吃飯
在父親呵護的那塊麥田里
我已長成飽滿的麥子
雖然八月暴曬
淚水浸泡
卻是幸福的一株
巴掌·木棍
為了把房檐和那群飛翔的夢
裝進我野心膨脹的童年
一只只雛燕
把命運的淚跌滿了他黃昏般的雙眼
又狠又重的一巴掌啊
印上我清醒的腮邊
從鉛字排成的日子里逃出
偷偷操起那把瘦弱的彎鐮
一捆捆玉茭使他
與沉默的木棍一同把我追趕
我跑走了跑走了的
還有那個星光嗚咽的夜晚
在巴掌和木棍之間
我默默地長大
從柳葉似的鄉(xiāng)村
走進城市的夢幻
可他卻遺憾地走了
帶著曠野里我再也聽不見的呼喚
于是我把一株松樹
作為他的記憶栽在窗前
那樹干一樣的木棍啊
那巴掌一樣的樹冠
和老爸聊天
爸 起來吃點飯吧
話音未落 發(fā)現(xiàn)
他遺像里的嘴角向上翹了翹
冬天 我在耐心學習孤獨
被流放他鄉(xiāng)的這幾年
您就是它和疾病輪班陪著
誰說陰陽分屬兩界
您走之后的夢里
咱倆常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
那年夏天日頭真毒
東北土路也開滿刺眼的白花
您遞給我半個消暑的西瓜
至今我口里還有香甜的味道
有一回我在村邊摔得天旋地轉
您愣是鐵著心不肯攙扶
還說 是爺們永遠不該跪著
我站起后至今再沒有彎過腰
爸 明代的解學士不想說話
如今的書和遍地莊稼一樣泛黃
放心吧 咱家門前那幾株嫩竹
世代都將翠綠 啥時候也變不了
回家
過大年時 天涯即咫尺
團圓的路多彎曲都將被走直
就是那些死去的靈魂
只要有照片在祭壇掛起
他們也能跨過連接陰陽的花瓣橋
紛紛回到家中與親人相聚
雖說今年好像從西晉來的大雪
穿越了近兩千載來勢緩慢卻格外高冷
梁祝孵化的蝴蝶們漫天飛舞
比許多頭顱上的思想還要潔白
凍結了遙遠的凝視
和每一寸方向
但爸爸您不必過慮
別說您的影像已成心底的烙印
并且 沿途的所有路口
都將亮起一支紅蠟燭
雪夜里咱家院里那盞經年的風燈
一眼就會認出您
母親簡歷
一歲時她母親去了天堂
八歲她開始用衣裳清洗村前的小河
十二歲她到草甸放牧豬和云朵
十七歲她成了懵懵懂懂的新娘
十八歲她嘗受兒子夭折的滋味
二十到三十五歲她屬于五個孩子
照料啼哭饑餓成長與黑夜
三十六到五十六歲她親近莊稼
玉米飽滿谷子沉實黃豆扎手
還有紫色的馬鈴薯花都很喜歡
五十七歲她進城像進了陌生的荊棘地
除兒子媳婦孫子連樓房也不認識她
沒有人叫的名字午后懨懨欲睡
好不容易她能找準東南西北
又遭遇老伴兒的失憶癥發(fā)作
到了七十二歲孩子們四處忙
她常一個人在花壇邊數(shù)花苞兒
陪伴太陽和地上自己的影子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
母親坐在沙發(fā)上睡著了
窗外一只鳥飛來了
一只鳥又飛走了
落葉的樹梢兒被寒冷棲滿
爸爸住到山坡上后
她就走進了無邊的冬天
往事里那些陳芝麻爛谷子
好像已先后睡去
為不把自己關在門外
她掛在脖子上的鑰匙
每天隨孤獨一起踱過斑馬線
燒菜 做飯 洗衣
生活之書的哪章哪節(jié)
全是地上爛熟的果子
沒有一顆再可以嘗鮮
兩片淺紅的布洛芬
負責骨頭一天的疼痛
電視機一個人大聲說著話
她坐在沙發(fā)上慢慢打起了鼾
當所有的節(jié)目謝幕時
睡意全消的她不住琢磨
月亮和太陽倒班兒太頻繁
一天短得還不到兩掛鞭炮
一輩子連支蠟燭也燃不完
唯有孫子千里之外的問候聲
才能像幾尾活蹦亂跳的魚
撞開她經常關閉的話匣子口
說自己身子骨硬朗不必惦念
她也會不時咂咂嘴
和鄰居嘮嘮孝順的兒子媳婦
嘮嘮啥叫幸福啥叫晚年
她瘦弱的手臂仍在風中揮動
第一次分離
我剛過十六歲
她三十九
我身前有神秘的大學牽引
身后有兩間土坯屋子站著
她高興兒子出去闖天下
莊稼地有金窩窩也不稀罕
和我說你胃不大好
在學校注意蓋好被子
少吃太硬的東西
望著遠處飛翔的小鳥
我咬破的嘴角向上一翹
回頭向她揮揮手
瀟灑地把背影留給九月
三十八年過去
又在路邊送別
我五十四歲
她正好七十七
我一面兒子將為人父
一面是母親白發(fā)日多
父親走了五年
我不安地叮囑這叮囑那
她總是平靜地說沒事兒
車已開出很遠
她瘦弱的手臂仍在風中揮動
孩子再大也要不斷出發(fā)
她得叫身體的柔軟處變得堅硬
人到老年必須學會告別
三九天乘著高鐵回家看望母親
窗外鵝毛大雪
一萬個美女的舞姿
仍無法讓急馳的高鐵分神
回家的方向是最快的方向
三九天 我乘著高鐵回家看望母親
前方亮起那盞不滅的風燈
也照不清天邊慚愧的云
直到父親臥床
從沒想過母親也需要照顧
父親能讓幾十畝莊稼在手上生長
男人病了也是男人
當有一天父親瘦成墻上那幀照片
母親突然又矮了幾分
燒菜洗衣購物日子紛亂
夜晚忍受著一百多米的孤獨
漫長的黑里不時傳來鬼魅的呻吟
兒女從遠方聚到身邊陪伴
她恨不得把天下美味都擺在桌上
夢中也疏淡了額頭越來越深的皺紋
可沒兩天她便把他們勸回家
說媳婦不敢單住孩子需要看護
自己這把老骨頭還硬朗得很
于是每晚端坐電視機前看天氣預報
成了我堅持最久的一個習慣
地圖上一些密密麻麻的小點兒
開始有了呼吸的表情和體溫
看完后再打個電話提醒她加減衣服
才能靜心在燈下讀書著文
五年 她以瘦弱的肩膀
扛起了一千八百多個多變的夜
按時電告兒女身體平安
一個人支撐著全“家”的溫馨
兒女流浪的足有休憩的碼頭
走在冰雪路上
也像懷抱一樣安穩(wěn)
一個人對一個人牽掛
一個地方對一個地方禱告
思念 原本是奔跑在天地間
眼睛酸澀永不老去的靈魂
快到站了 母親那雙滯重的小腳
是否已和花白的頭發(fā)一起站在路口
焦急地等待把風雪中的我辨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