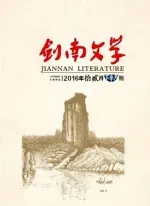一個人的烏托邦(組詩)
■張小外
安昌河畔
我的內心有無數(shù)攀爬的綠色藤蔓
它們不會開出紫色藍色的花
它們只在安昌河畔喝水唱歌
再把我的心裹緊一些
我遠望石頭欄桿在吹捧自己的堅固
我在河畔的水中和幾個鵝卵石游戲
直至它們少有的棱角劃破我的手指
問我要一些鮮活的血液恢復遠古的花紋
在二千二百多年后的綿州
大概和我親密的就安昌河畔的幾棵樹
我來它們說愛我要吻我
我走它們說留下請別走
我立于河畔苦苦等風
不管不顧時間溺亡
在黃昏中汲滿了生活汗液的棉衫
需要吹干
一到傍晚
一到傍晚
我擁有比火車更長的落寞
它的尖叫聲 它的奔跑聲
都在我的胸口上進行
將我的心反復摧殘
再不可能承擔轟轟烈烈石破天驚
一到傍晚
窗外無數(shù)的燈盞開始詛咒夜晚的盛大空虛
白天的綠樹變成了黑色的士兵
戒備森嚴
我的眼里塞滿惆悵
靜悄悄的吞噬眼前的一切
一到傍晚
我聽見鄰居出電梯的高跟鞋聲
以及一串鑰匙碰撞后
推開一道厚重的門
關掉尾隨一天的荒誕和憎惡
在伊犁吹冷風的男人——給父親大人
從四川綿陽撥號到新疆伊犁
我找那個正在吹冷風的男人
現(xiàn)在我有足夠多的愛意去愛這個瘦小的男人
這個破裂自己悲喜遠走他鄉(xiāng)的男人
這個給我完整予我生活意義的男人
這個從小到大甚少陪我的男人
現(xiàn)在還是站在他鄉(xiāng)的高大建筑物前吹冷風
安全帽是他的妻子兒女
汗水灰塵挖機貨車吊車構成他希望的鹽堿地
他一生都在占領丟棄遠離
讓我曾一度厭惡遠方這流沙樣的詞匯
對于他
我從小都愛得稀薄
像伊犁此時晝長夜短冷熱失衡的變態(tài)天
直到有一晚
我在夢里看見他的白發(fā)脫發(fā)向我走來
說這些年他給我的父愛并不冷峻缺失
一個人的烏托邦
他不能給你摘花摘云摘月亮
可你依舊愛他
就像戀著一個人的烏托邦
你愛他被歲月劃傷的面孔
愛他理不凈的胡茬
愛他新登陸的白發(fā)
推開門
他用醇熟的吻吻開你的心事
他用沒生銹的火熱燎原你的執(zhí)拗
像親歷黑夜的浪漫雅致
他永遠不在現(xiàn)實泊岸
他是你烏托邦的宿主
——紹興市公安局柯橋區(qū)分局安昌派出所側記(安昌派出所攝影 本刊編輯部報道)